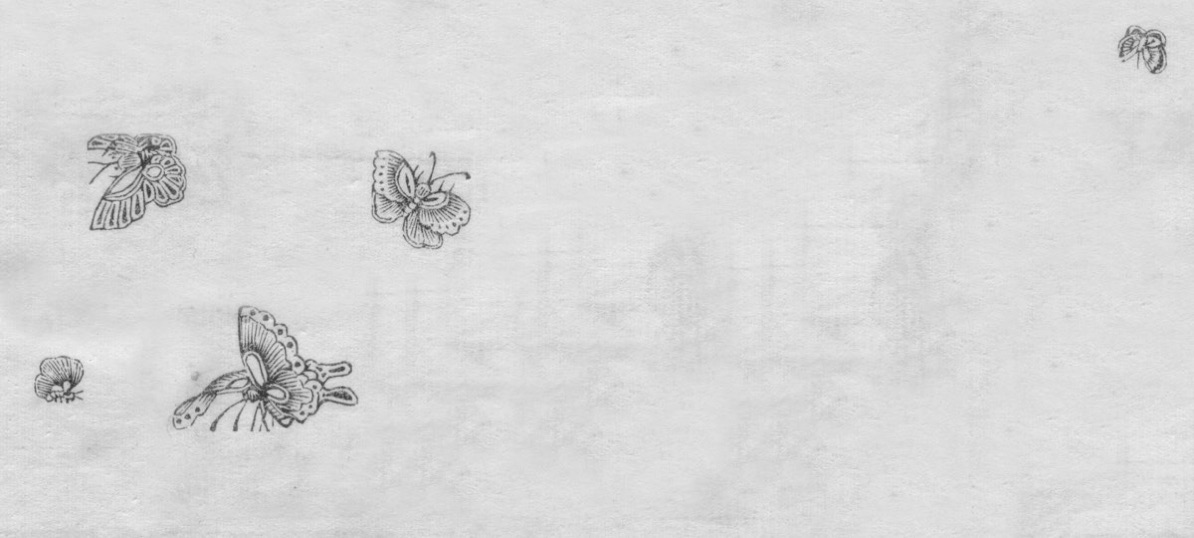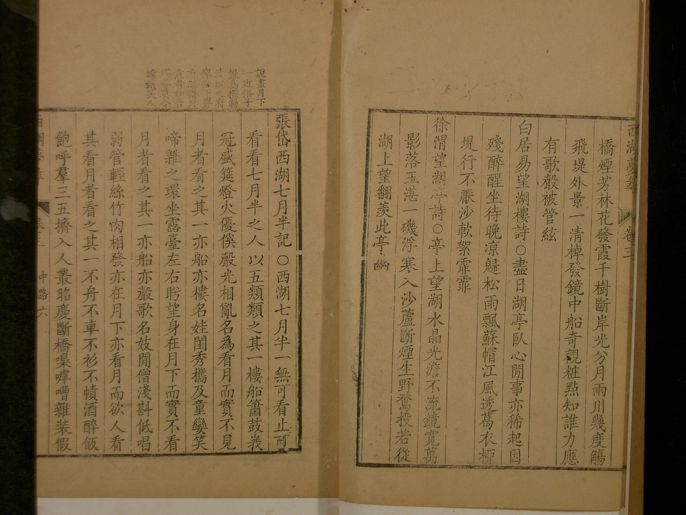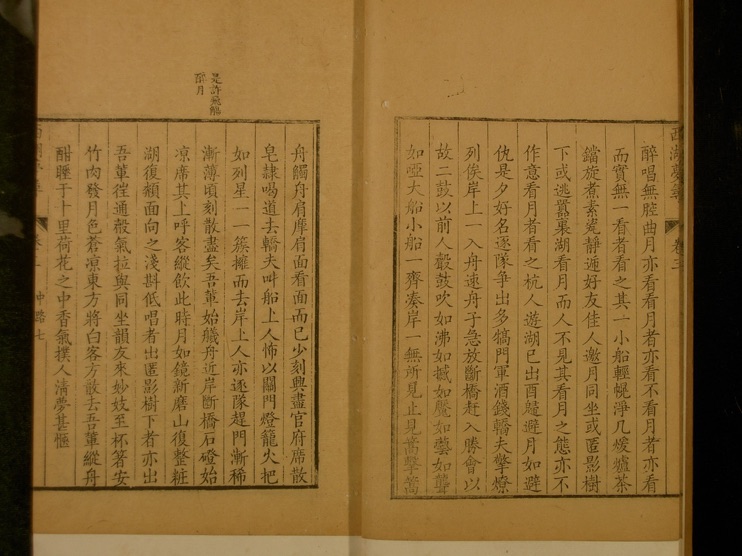他改做海上歸來的山中人,盛讚海味之美,聽得鄉人口水直流,爭相去舔他的眼睛。不幸的是,美味過舌即空。為了補救「空」所造成的「饞」(那種強烈要嚐到想像滋味而引發生理反應的念頭)而非「饑」(實際維生的進食提醒),他寫下夢中的故態、故有、故居,「舊夢是保」,用夢讓西湖的一派景色在「今余僦居他氏」、「今已白頭」、「今所見若此」之種種不堪的現狀之上,保住,端然不動。(《西湖夢尋》序)
以永恆的西湖地理為座標,分北西中南外五路,以自己為時間的終點,旁及、上溯曾到此一遊者的詩文,完全照著他認作「山水知己」的劉侗《帝京景物略》的體例安排,有門有類如志林,後來果然被收入四庫全書地理類,列在《四明山古跡記》和《穹窿山志》之間。
他有一批活夢友,經歷甲申之變的同輩們,如夢的感觸都曾在心和骨上銘下刻度。三十年後各自回看共同又分別經歷的大夢,心境大不同。當張岱以《西湖夢尋》託付寫序時,他們對宗子舊夢的態度五個裡有兩個不以為然。與其是針對癡夢張生,還不如說他們表白了對執著過去的私心情:割捨、淡置、變化。
其中李長祥的序最特別。
多年後,為張宗子的西湖舊夢寫序,他氣概不減,不欣賞退卻入懷舊的弱心態。他說,甲申三月,一夢蹺蹊,三十年來如魘若囈,身旁的人都要上屋頂去招他的魂了,哪還理會他夢中所有,更何況更遠的夢中所有?要想用舊夢去保故有,完全不可靠,因為人們對舊夢不感興趣。
所以要變舊夢成為無關「想」和「因」的全新自起之夢。就像蘇東坡懷疑揚雄是否真存在的激進精神,張陶庵筆下的西湖在近日的西湖完全找不到,那麼前朝是否真有那個西湖?明季西湖中真有張陶庵?也就是否定張宗子筆下西湖的存在,再否定作者在那個不存在的西湖中的根本存在。抹去作者、時地、動機——歸零——從懷舊的遲滯局限裡釋放出《西湖夢尋》供後來者自由取決——一如宗子三十年前在《石匱書》經籍志給《夢憶》安排的歸屬:小說。
名根舍利被新夢論輾壓粉碎。
回頭看,李長祥的新夢論,其實,是預言。